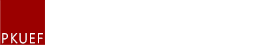“把我的歌帶回你的家,請把你的微笑留下。”
十年過去,這句真摯的歌詞,也許是對這所院子、這群人們最好的注解。
又是一個新學(xué)期。北大靜園四院的門口,人群又熱鬧了起來。
新生入學(xué),不同顏色皮膚的年輕人來到庭前,駐足,交談,留影。他們是北大燕京學(xué)堂第十批新生。和著庭前的歡聲,燕京學(xué)堂也迎來了她的第十個生日。
自十年前成立以來,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來到這里上學(xué)、生活,林林總總,有一千多人。他們把這里的所見、所知、所感,帶回了自己出發(fā)的地方。他們則在此歡笑,擁抱,同時把這里也當(dāng)作了自己的第二個家。
正如那首流傳甚廣的中文歌曲所唱:請把我的歌,帶回你的家,請把你的微笑留下。歌聲與微笑,像音符一樣流淌,貫穿這十年的空間與時間。
換一片土壤,生長
古裝劇《蕓汐傳》上映后,安君傲(Antonio Roberto Quiroz Soto)“二刷”了。一開始從朋友圈里刷到幾張劇里的截圖,他就被場景和服裝吸引了。問了朋友劇名后,他打開視頻軟件開始追劇,這也是他第一次看中國古裝劇。
小時候,這個墨西哥小男孩就對中國古代文化感興趣。高中時,他開始學(xué)習(xí)中文,在孔子學(xué)院的“春晚”上表演了節(jié)目。也是在這里,他第一次聽說“北大”,并獲得了來中國學(xué)習(xí)的機(jī)會。
第一次來北大的那天,學(xué)校里正在舉辦國際文化節(jié)。感受著校園的氛圍與情景,安君傲做了個瘋狂的決定:從墨西哥最好的大學(xué)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xué)退學(xué),來考北大。經(jīng)過艱苦的努力和激烈的競爭,他成功了。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學(xué)燕京學(xué)堂,成為一名中國學(xué)研究生。
由于一直對歷史和考古感興趣,來到燕京學(xué)堂的第一個學(xué)期,安君傲就選修了考古文博學(xué)院張劍葳老師開設(shè)的“中國古代建筑技術(shù)史專題”。他和同學(xué)們一起前往陜西省參加調(diào)研,第一次以非游客的身份,去認(rèn)識中國的歷史文明。回來后,他寫了一篇關(guān)于中國和墨西哥金字塔形結(jié)構(gòu)比較的論文。
張老師給了他許多建議,并鼓勵他繼續(xù)探索這一話題。在與張老師長談過幾次后,這個從小就有考古夢的墨西哥男孩重拾了最初的專業(yè)夢想,最終,從進(jìn)入燕京學(xué)堂時的政治與國際關(guān)系的專業(yè)方向,轉(zhuǎn)專業(yè)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考古方向。
這一年,正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個拉美小伙兒,在中國實現(xiàn)了自己的考古夢。

2020年7月,安君傲作為畢業(yè)生代表在北京大學(xué)畢業(yè)典禮上發(fā)言
在一次荷蘭圖書館清倉大拍賣中,還是高中生的史凱恩(Koen Smeets)注意到了一本滿是灰塵的書,書名為《世界歷史:中國》。這個荷蘭小伙在好奇心的驅(qū)使下,一路來到中國,在燕京學(xué)堂研究中美學(xué)術(shù)關(guān)系。
史凱恩研究的是1978年中美學(xué)術(shù)關(guān)系重新建立這一課題,為了這個課題,他專門創(chuàng)立了一個播客,名叫“中國通”(China Hands) 。做播客時,他采訪了許多嘉賓,雖然這些人能夠流利地使用中文、并在中國生活了許久,但是他們都表示自己所學(xué)只是冰山一角,中國的文化、社會、歷史、發(fā)展是浩瀚無垠的海洋。史凱恩發(fā)現(xiàn),只有到了中國學(xué)習(xí),與中國人相處、交流,才能真正地認(rèn)識到中國。
“如果沒有北大燕京學(xué)堂,我就沒有機(jī)會親身體驗中國。”親身在中國逛故宮,逛大街,跟老師同學(xué)們吃飯聊天,史凱恩覺得,“中國人是我的老師。”正是通過這些親密的經(jīng)歷,人們才能對一個國家的文化和社會有深刻的了解。

史凱恩第一次來到故宮
這里的年輕人們,朝著各種方向伸展自己的熱愛。畢業(yè)于英國牛津大學(xué)的柯若波(Robert Krawczyk)參加新絲綢之路項目,從格魯吉亞阿納克利亞出發(fā),一路到達(dá)上海,還受到中國科幻小說和俄羅斯宇宙學(xué)說的啟發(fā),為blip.land網(wǎng)站拍攝視頻;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的陳沅增(Yuan Zeng Ashley Tan)會說14種語言;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xué)的何依然,曾在美國國會實習(xí),也在蘇格蘭小學(xué)擔(dān)任過漢語教師......誕生自不同的文化的生命個體,在這片中國的文化土壤上,汲取獨(dú)特的養(yǎng)分,恣意而多元地生長。
碰撞與交響
來自美國的毛敬宇(Joe Mazur),在2015年從哈佛大學(xué)畢業(yè)后,來到了燕京學(xué)堂。“來這里的外國學(xué)生都是對中國問題感興趣,希望以開放的心態(tài)將自己浸染到一個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中。”
跨學(xué)科教育是北大燕京學(xué)堂倡導(dǎo)的學(xué)習(xí)和培養(yǎng)方式之一:既包含對于文史哲等中國古典學(xué)問的研究,更著眼于對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觀察和思考。學(xué)堂設(shè)立了政治與國際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與管理、法律與社會、哲學(xué)與宗教、文學(xué)與文化和歷史與考古六個專業(yè)方向,60余位教師為學(xué)生開設(shè)了48門中英文課程。毛敬宇選擇的是政治與國際關(guān)系方向,而這個方向的課程則改變了他對中國如何看世界的固有印象。
在學(xué)堂的生活,不僅僅是上課、學(xué)中文,更多的是一種經(jīng)歷,其中的許多東西“是我作為游客時不能體驗到的”。比如,毛敬宇發(fā)現(xiàn)中美兩國人際關(guān)系的微妙不同:在美國,“如果我去買杯咖啡,我和營業(yè)員會互相很熱情地打招呼。”而在中國,人們當(dāng)然也很友善,但“比如我去買東西,我和營業(yè)員之間只會有一種商業(yè)交易的互動,我們不會熱情地互相打招呼”。但是當(dāng)他和中國人成為朋友后,“我們之間的親密度會超過在美國朋友親密的程度。”
在中國學(xué)習(xí)與生活使他“處于一個有利的位置”,可以看到東西方各自的優(yōu)勢。“我理解他們采取不同方式的道理之所在,并且希望在以后的生活與職業(yè)道路中,我可以綜合這兩者”。

毛敬宇在燕京學(xué)堂
越來越多的世界青年在這樣的碰撞中迸發(fā)了新的思考。本科畢業(yè)于芝加哥大學(xué)的王黎颯(AlizaWarwick),看到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很好奇為什么中國會有這么多父母給孩子找對象,便以此為內(nèi)容寫了畢業(yè)論文,并因此報考了燕京學(xué)堂,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國人。英國的施睿建(James Ashcroft)畢業(yè)于倫敦大學(xué)學(xué)院,來燕京學(xué)堂不久后,就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有很多茶,龍井茶、普洱茶,還有宋朝的“茶圣”陸羽,但在國際市場上,為什么是國外的立頓紅茶更有市場呢?這引發(fā)了他的思考。歷史感和時代感交織在一起的問題,在世界青年的腦海中此起彼伏。

2017年9月,2017級中外新生代表合影
陳正勛作為學(xué)堂的首屆中國學(xué)生,畢業(yè)后作為福州政府的經(jīng)貿(mào)代表赴印尼開展工作。受益于學(xué)堂的教育經(jīng)歷,他能夠更好地理解“萬島之國”的多元世界。美國駐華大使鮑克斯、泰國公主詩琳通等國際嘉賓曾訪問學(xué)堂,高盛亞太區(qū)主席施瓦茨為他們演講;自己作為王賽老師發(fā)起的“益橋未來公益領(lǐng)袖培養(yǎng)計劃”創(chuàng)始團(tuán)隊的一員,獲得了蓋茨基金會等機(jī)構(gòu)的支持;和燕京學(xué)堂同學(xué)、來自美國的合伙人Kyle一起,建立起“OneBank”品牌并與區(qū)域性銀行達(dá)成合作試點(diǎn)……通過這些經(jīng)歷,他獲得了一種集體認(rèn)同,一種對學(xué)術(shù)共同體、中外人文交流共同體的集體認(rèn)同。

陳正勛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燕京學(xué)堂開設(shè)核心必修課“實地調(diào)研”“轉(zhuǎn)型中的中國”等課程,鼓勵師生把中國大地作為課堂,發(fā)現(xiàn)書本以外的中國研究。幾年來,師生的足跡從北京的三里屯街道、義烏的小商品城,到貴州的苗寨和重慶的高科技園區(qū),遍布全國。他們親身體驗、親自交流,親眼看見了一個全面而亦古亦新的中國。
來到燕京學(xué)堂讀研究生后,白俄羅斯女孩蘇小小(Ekaterina Kaligaeva)的專業(yè)是中國學(xué)。她注意到國際上一直存在著對中國有誤解的聲音,“我覺得對中國特別不公平,因為我看到了不一樣的中國。”她參加了“知行中國·相約甘肅”的研學(xué)之旅,親眼看到中國的青山綠草,親自踏過甘肅的朔漠清泉,她才真正理解了“百聞不如一見”的意義。
“當(dāng)那些沒有來過中國的人要用一個‘標(biāo)簽’來概括中國的時候,他們又怎能想到中國文明中的歷史與地域要素所創(chuàng)造出的豐富與璀璨……”再對國際友人聊到中國時,她都會通過第一視角去給他們看照片、視頻,“這些會比看一些官方的報道更加生動。”

蘇小小參加 “發(fā)現(xiàn)中華之美——在華外國青年‘知行中國·相約甘肅’研學(xué)活動”在敦煌鳴沙山留影
“如今,中國可以說是我的第二個家鄉(xiāng)了。”蘇小小說。
生活與生趣
每一年,都有形形色色的多才多藝的年輕人們,在這里用不同的聲音、語調(diào),聊天爭論,以不同的表情、姿態(tài),探討互動。交流碰撞出了各式各樣的奇思妙想,大家便開始一起“搞事情”。
“全球青年中國論壇”,就是學(xué)生們共同搞的一件極有意趣的“大事”。“全球青年中國論壇(Yenching Global Symposium)”,被稱為“YGS”,作為燕京學(xué)堂的旗艦活動,由學(xué)生們一手策劃運(yùn)營,自2016年起,在每個春天舉行。持續(xù)三至四天的會期內(nèi),世界各國青年與業(yè)界專家,在此探討與中國和全球有關(guān)的關(guān)鍵性話題,嘗試為世界提供一種解決的可能性。
每年的“YGS”,主題名都是最令人期待、也最有意思的:2017年,論壇主題為“創(chuàng)‘新’:中國創(chuàng)新的身份|Xinnovation: Identity of Innovation in China”,結(jié)合“xin”這個題眼,各國青年結(jié)合自身學(xué)習(xí)中文拼音過程中的體驗,給“xin”字選了四種寫法,分別從“心、新、欣、昕”四個角度,延伸出不同意涵的討論。2018年,論壇主題為“復(fù)興:中國在全球未來中的旅程|Renaissance: China's Journey in a Global Future”,學(xué)生們同樣從題眼中拆出了“ren”的諧音,分別從“人、認(rèn)、任、仁”四個維度,進(jìn)行更深更廣的意義探討。2019年,論壇主題為“我們:重述中國故事|Wǒmen: Retelling the China Stories”,其中“women女性”與中文拼音“Wǒ Men我們”相結(jié)合,巧妙地開拓了一個全新維度。2021年的主題“同舟共濟(jì) 再創(chuàng)未來|Shared Renewal: Recoupling East with West”,則在視覺設(shè)計上,將同舟共濟(jì)的漢字“同”字,與“Shared”的英文單詞,疊合在一個中心,看上去像極了一個同心圓,圈在人們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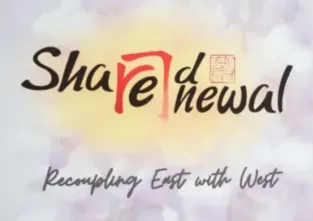
不管是“諧音梗”或是“文字游戲”,藏在字里行間的意趣,折射出的是不同文化碰撞出的創(chuàng)造力,這股力量又在不一樣的形式間不斷流淌,反哺到生活中去。
2021年,一場以門為核心意象的跨學(xué)科文化展覽“我,門”在燕京學(xué)堂呈現(xiàn)。兩排夜燈被安置在靜園四院的小徑兩旁,那是為下晚自習(xí)的同學(xué)專門設(shè)計的。燈光被調(diào)到適度,因為“要保持中國園林中詩的意蘊(yùn)”。窗上用紅色元素裝點(diǎn),當(dāng)陽光照射進(jìn)來,光影投在墻上,形成了一只美麗的蝴蝶。

蝴蝶從園中飛來,流連,又落在園中。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在全球五大洲的年輕人身上輸入,新的創(chuàng)造又在此不斷出現(xiàn),生長。
因為愛
2018年的夏天,美國姑娘康美麗(Emily Conrad)從北大燕京學(xué)堂畢業(yè)了。第二年,她和中國小伙艾天結(jié)了婚。
2015年,康美麗來到中國攻讀國際關(guān)系專業(yè),就是希望能超越西方的視角,從多級角度、更全面地理解國際。這種嘗試,從最初的求學(xué)生活里,被一路帶入了婚姻生活,乃至整個人生。
丈夫艾天是中國人,康美麗免不了要學(xué)習(xí)中文。日常交流里,兩人因為語言不通發(fā)生過溝通不暢和誤解,也因此察覺到類似的隔閡與矛盾,在當(dāng)前的地緣政治事務(wù)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原來國與國、人與人,都是一樣的道理。
在北大上學(xué)期間,業(yè)余時間熱愛詠唱歌劇的她對中國的傳統(tǒng)音樂也癡迷起來。畢業(yè)前夕,她在燕京學(xué)堂成功地舉辦了自己的音樂會。現(xiàn)在的業(yè)余時間里,她也會跟丈夫去劃龍舟、唱中國歌曲。與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燕京學(xué)堂一樣,康美麗也希望自己和丈夫能成為“兩座溝通不同文化的橋梁”。

現(xiàn)在,康美麗的中文老師,是自己的婆婆。婆婆教她中文,也向她學(xué)習(xí)英語,彼此已經(jīng)沒有交流問題了。“實在不行就用中文”,她爽快地笑。婆媳倆出門逛街時,手拉手臂挽臂,像一對閨蜜。

康美麗和婆婆逛街
無獨(dú)有偶。畢業(yè)于柏林自由大學(xué)的德國姑娘瑞奇(Ricarda Brosch),她是燕京學(xué)堂第一屆學(xué)生。在這里,瑞奇遇到了她未來的丈夫——他正是第一屆全球青年中國論壇的代表。八年后,兩人結(jié)婚了,現(xiàn)在有了一個女兒,她從第一天就學(xué)會了中文。“這就是我在燕京學(xué)堂所經(jīng)歷的重要意義。”這是一種改變生活的經(jīng)歷,更塑造了一個人的人生。

瑞奇
有人在這里收獲愛,有人則因愛而來到這里。蘇小小與中國的緣分,便是由父母開啟。在讀初中的最后一年,她在爸媽的引領(lǐng)下接觸到了中文,因為爸媽覺得“學(xué)習(xí)中文對未來發(fā)展很有幫助”,并鼓勵她報名孔子學(xué)院的零基礎(chǔ)中文班。2017年,“漢語橋”比賽在湖南長沙舉辦,沉迷中國茶文化的媽媽為蘇小小準(zhǔn)備了兩個行李箱,一個箱子用來裝比賽所需的服裝用品,另一個箱子則專門為媽媽帶回中國的茶葉。在媽媽的影響下,蘇小小逐漸了解中國文化及其歷史,更加深了對中國的感情。

蘇小小身著華服
燕京學(xué)堂的同學(xué)們開玩笑說,以后去世界上哪個地方旅行,都可以找到一張沙發(fā)了。“任何一位現(xiàn)在的學(xué)堂同學(xué),五年十年后都仍然會是我的朋友。我現(xiàn)在記得每一個人的名字,他們從哪里來。我甚至可以告訴你某個人的寵物叫什么!” 第一屆燕京學(xué)堂的俄羅斯學(xué)生愛琳娜(Anastasiia Ilina)大笑著說。
同為第一屆學(xué)生、畢業(yè)于普林斯頓大學(xué)的美國學(xué)生艾文(Cody Abbey)也說:“我的中國朋友已經(jīng)比我的美國朋友多。”他在學(xué)堂十周年時再次回到了北大。走進(jìn)東門的那一刻,熟悉的地點(diǎn)和場景喚起他的回憶。“我記得當(dāng)我走過跑道和邱德拔體育館時,北京大學(xué)自行車隊的緊張訓(xùn)練;我記得我和朋友在未名湖邊散步時的沉思;我想起了我們曾在勺園舉行的許多生日聚會和節(jié)慶活動。”他形容起這座園子對自己的意義:“就像家一樣。”

艾文
“我們這些人不會永遠(yuǎn)在中國,但是我們的心里永遠(yuǎn)會有中國。”這是所有燕京學(xué)堂同學(xué)們的共同心聲。

新學(xué)期伊始。陽光透過窗戶照進(jìn)來,落在一屋子膚色各異的年輕面孔上。背著書包、端著咖啡的學(xué)生們進(jìn)進(jìn)出出,呼朋引伴。英文的寒暄聲響起,夾雜著笑聲。
又一屆畢業(yè)生已經(jīng)離開,新一屆學(xué)生已經(jīng)到來。他們在此,留下笑容,帶走歌聲。明天這歌聲,飛遍海角天涯。明天這微笑,將是遍野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