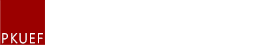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繞過那條充斥著各種“成功者要達到的10條標準”之路,走向一間不大的屋子,選擇簡樸甚至單調(diào)的生活方式,只為在自己所屬的專業(yè)領(lǐng)域再向下多挖一點,想著自己能不能再為社會創(chuàng)造些什么。北京大學(xué)城市與環(huán)境學(xué)院陶澍老師所帶領(lǐng)的研究組就是這樣一群人,一群為科研夢想堅守的人,作為地表過程分析與模擬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組員,他們在新時代完成著自己的夢。
聚焦:陶澍重點實驗室
隸屬于北京大學(xué)城市與環(huán)境學(xué)院的陶澍重點實驗室由陶澍院士指導(dǎo),主要項目是“大氣PM2.5傳輸模擬”和“農(nóng)村能源調(diào)查”。實驗室目前由一位博士后、八位博士生、四位碩士生、四位本科生構(gòu)成。
作為幾個課題小組中資歷最深的博士生之一,韻瀟致力于中國農(nóng)村生活能源對于大氣污染和人群健康的研究。事實上,在很多環(huán)境研究領(lǐng)域中,農(nóng)村地區(qū)往往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tài),但陶澍告誡學(xué)生們,不能忘了農(nóng)村。

實驗室成員下鄉(xiāng)調(diào)研
在城市里,人們經(jīng)常查看當天的空氣質(zhì)量,也會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抱怨污染的情況。城市人群集中、汽車尾氣排放量大、嚴重的霧霾天氣等都會成為人們更擔(dān)心城市空氣污染的原因,而農(nóng)村給人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海子詩中的那般,“活在這珍貴的人世間,水波溫柔,陽光強烈”。
“但實際上農(nóng)村的大氣污染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城市的更加嚴重,”韻瀟說,“比如室內(nèi)污染,城市里只有做飯會產(chǎn)生污染物,大多數(shù)家庭有污染也馬上被油煙機抽走了。但在農(nóng)村,北方很多地方還在用使用固體燃料的家庭爐灶,爐子在房間里面燒,刺鼻的氣味在門外都能聞到。”
這種生活源對大氣的污染程度常常被人們低估甚至遺忘。舉個燃煤的例子,雖然每年電廠和工業(yè)用煤的消耗量大約比生活用煤高一個數(shù)量級,但事實上生活源有其自身特征,消耗量小,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單位質(zhì)量或體積能源燃燒產(chǎn)生污染物的質(zhì)量)卻很高。國家往往通過限制電廠和工業(yè)用煤的量以期達到大氣污染的治理效果,但據(jù)韻瀟的研究來看,若是從生活源切入,只需減少相當于電廠或工業(yè)的大約十分之一的耗煤量,就可以達到接近的減排效果。
這些研究依賴于課題組成員們多年扎根農(nóng)村開展的數(shù)據(jù)測量和搜集工作,覆蓋中國大陸31個省,幾乎全部的地級市(暫時未包括港澳臺地區(qū))。數(shù)據(jù)收集后反饋給課題組里負責(zé)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建模的同學(xué)們,應(yīng)用于大氣污染分布模型,通過模型的模擬可預(yù)測某時某地大氣PM2.5的濃度。
這種使用大氣化學(xué)傳輸模式模擬大氣PM2.5濃度的研究方法,讓研究小組不僅能以此預(yù)測未來一段時間大氣的污染狀況,而且可以推知過去的大氣狀況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健康風(fēng)險。“我們通過能源調(diào)查和排放因子測量希望得到一個統(tǒng)籌的數(shù)據(jù),從宏觀上知道每個市級城市與農(nóng)村居民生活各消耗了多少能源、排放了多少污染物,進而提出相應(yīng)的減排措施。”
走近:“我”與實驗室
“讀博這幾年雖然有些不順利的地方,但總體還是非常好的。”談起自己的博士生涯,韻瀟沒有訴說科研工作的枯燥和無聊,對科研的強烈興趣和取得科研成果的成就感讓他整個人神采奕奕。“我覺得做科研是一件挺高興的事情。一想到我的研究成果能幫助到別人、能對社會產(chǎn)生一點正反饋的話,就會覺得很滿足,這算是實現(xiàn)人生價值了吧。”
對科研要有熱情是陶澍實驗室的“挑人標準”。正在就讀研究生二年級的邱有為自認為本科的成績不算特別優(yōu)秀,但他對科研的強烈興趣、對“冷板凳”的無所畏懼,打動了陶澍老師。而這種興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本科階段時受陶澍影響的結(jié)果,邱有為說:“很多時候我都被陶老師的敬業(yè)所影響,想要向他學(xué)習(xí),用他對自己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在外人看起來,做科研是件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去思考鉆研,在枯燥的過程中只能等待結(jié)果的一點點愉快,轉(zhuǎn)而又要投入到下個研究階段的事情,但是對于今年剛成為陶澍博士生的徐浩然而言,“做科研不僅是對外部事物的永恒探索,也是對自己生命的補充和完善。”陶澍今年已經(jīng)68歲了,但對科研事業(yè)的激情和熱愛使他仍保持著像年輕人一樣蓬勃的精神狀態(tài)。徐浩然也正是被陶澍這種年輕的、永遠精力充沛的狀態(tài)所感染,決定選擇科研道路并且打算為之奮斗一生。
“陶老師那種年輕的感覺,讓我覺得做科研可以讓你的生命時間得到延長,年輕的日子會比別人多很多。高校的教授們五六十歲的時候,其實狀態(tài)跟三四十歲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有了科研能力的提升和更多經(jīng)驗的積累。他們一直在和二十歲到三十歲左右的學(xué)生們接觸,他們也是在做三四十歲的時候做的日常工作和活動,所以我覺得可能他們一輩子都會那么年輕。”

陶澍和部分畢業(yè)學(xué)生合影
深入:家一般的團隊
從“小師弟”邱有為、徐浩然到“大師兄”韻瀟,一群認真嚴謹、青春熱血的年輕人聚集在了同一個科研實驗小組。成員們可能對自己的研究軌跡懷有不同的愿景,但相同的是他們都被陶澍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以及對科研的無盡熱愛,這也是他們加入課題組的原因所在。
科研對他們而言蘊涵著無窮樂趣,尤其在這樣一個氣氛融洽的科研團隊之中。“整個團隊就像家一樣”,韻瀟這樣形容實驗室的氛圍。在這個大家庭中,陶澍老師就像他們的大家長,領(lǐng)導(dǎo)和統(tǒng)籌著實驗室整個的科研工作,同時也是他們?nèi)松念I(lǐng)路人,身體力行地踐行身為一名科研工作者應(yīng)有的鉆研精神。
“陶老師沒有手機,也不用微信,他和別人聯(lián)系只發(fā)郵件,出門都和大家在一起。”邱有為說,陶老師在閑暇之余有時會和組員一起下棋,“大家都不會讓著他,我們‘放水’老師會責(zé)怪我們,但其實他的水平比我們高很多,我們很難贏他。”
陶澍還喜歡和學(xué)生們一起打球、爬山。“老師精神很足,爬山比年輕人還快。而且我們春秋游老師都是騎自行車去的,他騎車很快,我只能騎著電動車跟著他。”韻瀟說到這里笑得很害羞,“老師的車很舊,車筐都快和車分離了,他也不讓我們給他換車,所以我就給他換了個車座和車筐。”

實驗室部分成員合影
不管年齡多大、能力多強,陶澍始終保持著年輕、沉穩(wěn)的心態(tài)以及對科研的熱情,組織著這個“家一般的團隊”。作為一個不常開組會的團隊,基于的是陶澍合理分工以及團隊無間的交流,對于他們來說,科研精神是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勇攀高峰。也許正是這樣的共識,使得他們的團隊更富有凝聚力和創(chuàng)造力。
致敬:冷板凳的堅守
“3個人拖5個大箱子,裝200個檢測儀”“3次大巴,轉(zhuǎn)車6個小時,晚上10點半到調(diào)研的村子”“7天調(diào)研100戶人家”……這是外出調(diào)研同學(xué)的常態(tài),以至于到后面嗓子都說不出話來了見到村民還是張口就問:“叔叔/阿姨好,您家主要使用什么類型的能源取暖和做飯……”
科研并不是由那些遙不可及的群體組成,再冠以外界神圣化描述的一件事。更多的是一群人繞過那條充斥著各種“成功者要達到的10條標準”之路,而走向一間不大的屋子,選擇簡樸甚至單調(diào)的生活方式。
“當時師兄在電線桿上裝研究儀器,他讓我準備好一塊木板,萬一觸電,就用木板把他打下來。”韻瀟說。研究者為了在所屬的專業(yè)領(lǐng)域再向下多挖一點、再看看自己能為社會發(fā)展做些什么時,有時甚至都忘了自己可能面臨著危險。
當問起為什么不去找工作而是決定做科研時,徐浩然說:“科研是一個積累的過程,沒有明確的結(jié)束節(jié)點,我們要為它努力一生。”他認為科研和工作的區(qū)別可能在于所處節(jié)點的反饋不同。工作是在一段時間內(nèi)好好做手頭的任務(wù),甲方滿意后在社會上換取相關(guān)的資源進而轉(zhuǎn)向下一個項目再生產(chǎn)。但科研不一樣,沒有明確的節(jié)點告訴你這件事已經(jīng)完成,每一個小課題的結(jié)束又是新任務(wù)的開始。
在時間的流逝中,科研一方面讓你對這項事物有了不斷地新認識,為社會對于該事物的認識做出了積極的正反饋;另一方面,你在探索這項事物的進程中,這件事讓作為個體的你也變得更加完整,補充著自己的生命,讓精神有所寄托。

實驗室成員在火車站調(diào)研
“不斷地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攀登高峰,并且要在其中找到快樂。雖然很多時候并不快樂,但你需要找到自己的快樂。”韻瀟補充道。
當被問及為什么選擇做科研,韻瀟這樣說道:“這是最好的時代,我覺得作為北大人應(yīng)該要有社會擔(dān)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