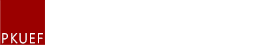未名湖畔,花韻化于墨香,蟲鳴鳥語難掩朗朗書聲。
新疆南疆,廣袤無垠,風吹日曬,是一派詩情豪邁。
幾代人的青春、擔當和夢想,就在這樣的反差之中葳蕤生光。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北京大學畢業(yè)生奔赴南疆,從祖國的心臟來到天山腳下,用一場青春時代的“逆行”,踐行自己的心中的呼喚——
“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沿著洪水滔滔的葉爾羌河走了十個小時,還錄了一段遺言”

畢鵬
畢鵬,男,元培學院2005級本科生,教育學院2010級碩士生。
本科畢業(yè)后赴西藏自治區(qū)農牧廳工作,2012年選調到河南省滑縣基層鄉(xiāng)鎮(zhèn)工作,后調任新疆塔什庫爾干縣,現供職于喀什地區(qū)大數據局。
僅僅來到塔縣一百多天,畢鵬就對這里的情況了如指掌了。
塔縣是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的簡稱,是我國著名的邊境縣,面積2.5萬平方公里,僅有4萬人居住,卻有著888公里長的邊境線,跟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三個國家交界,著名的喬戈里峰就在這里。
“我們塔縣,我們塔族……”是畢鵬的口頭禪,一說起塔縣,他便兩眼放光,對這里的風土人情更是如數家珍,無所不知。
這些了解并不是道聽途說抑或是信口杜撰,全然是畢鵬一步一步體驗出來的。

畢鵬調研當地鄉(xiāng)鎮(zhèn)
到塔縣的第二天,畢鵬就去了下面最遠的鄉(xiāng)鎮(zhèn)布倫木沙,勸住在山里的群眾搬下山。
路途遙遠,他們先騎著毛驢,到了毛驢過不去的地方,就必須要步行。
“我們沿著洪水滔滔的葉爾羌河走了十個小時,中間有一段路實在是太險了,我當時真的覺得可能會掛了,還錄了一段遺言呢……”
更嚴重的問題出在飲水上。
在他們去的路上有兩個泉水點可供補給喝水,而在回來時只有一個泉水點,“渴得不行時候只能喝葉爾羌河水,回來嘴都腫了好些天。沒有水的時候,我們真的經歷了‘上甘嶺’,大家分一瓶水,每人一口,都很自覺自律,跟向導和一起去的同志都成了過命的交情!”

北大畢業(yè)時的畢鵬與在南疆工作后的畢鵬
如今,戴著眼鏡、手曬得脫皮、膚色黝黑的畢鵬儼然與當時在北大讀書時的樣子大有不同,但他從未后悔。
正如被他牢牢記于心間的那段林毅夫老師曾講過的話——
“今天我們從這里出發(fā),
只要民族沒有復興,
我們的責任就沒有完成,
只要天下還有貧窮的人,
就是我們自己在貧窮中,
只要天下還有苦難的人,
就是我們自己在苦難中!
這是我們北大人的胸懷,
也是我們北大人的莊嚴承諾!”
“以后我就是您的孩子!”

鄭明鳳
鄭明鳳,湖南邵陽人,出生于1990年。2013年保送到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環(huán)境與能源學院攻讀碩士研究生,主修水環(huán)境科學。
畢業(yè)后,他遠赴新疆阿克蘇地區(qū),目前在新疆庫車縣烏恰鎮(zhèn)工作。
到祖國基層去的理想在鄭明鳳心中由來已久。
鄭明鳳生長于湖南邵陽的一個山村,少年時期的他也常常夢想著能夠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后來,他離開了湘中的那座邊遠小城,到大城市中進行本科及研究生的學習。
“想要做的其實是一種回饋。”回憶起少年時光,鄭明鳳的內心充盈了感激,“不是為了擺脫貧困地區(qū),而是為了幫助貧困地區(qū)擺脫貧困。”
很多邊遠地區(qū)的物質供應都嚴重不足,遑論文化滋養(yǎng)、精神追求。
“我想要讓邊遠地區(qū)也享受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紅利。”
2016年的畢業(yè)季,如同千千萬萬的應屆畢業(yè)生一樣,鄭明鳳面臨著選擇。當時可以解決北京戶口的金融央企總部等十余份offer擺在他面前,每一份都令人生羨。
同大城市相比,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而言,南疆都只是選項之一,且排序一般不會靠前。
但是,鄭明鳳想要奔赴邊疆、下到基層,到最艱苦的環(huán)境中實現自我價值,奉獻社會。
當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鄭明鳳想起了在陜西富平的調研生活,想起了知青時期的總書記“一孔窯洞、一盞煤油燈、兩箱圖書、一片熱土”的日子,也想起了總書記的一句話“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際遇和機緣,都要在自己所處的時代條件下謀劃人生,創(chuàng)造歷史。”

最初被分配到庫車縣時,不會說維吾爾語的鄭明鳳和一些不會說漢語的當地群眾也遇到了一些交流的困難。如果連最基本的交流都無法達成,單純地靠第三方的翻譯,又怎么能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呢?為了更快地融入當地的生活,鄭明鳳給自己取了維吾爾語的名字jasur,然后從最基本的32個字母開始學,并且每天都會用自創(chuàng)的“一五一十”法來學習維吾爾語。最初接觸維吾爾語的鄭明鳳,對周圍的一切都充滿了強烈求知的欲望:“我一有空就去找老鄉(xiāng)聊天,這叫啥、那叫啥,追著人家問。”“我感到收獲的不僅是學會了一門語言,還有老鄉(xiāng)的親近和信任。”
也許他也不知道,這個他所負責的村莊里的這群村民,已經逐漸變成了他話語中的“老鄉(xiāng)”,平時的見面打招呼中,已經宛若親人。

北大畢業(yè)時的鄭明鳳與在南疆工作后的鄭明鳳
鄭明鳳說:“我要努力做群眾心里的兒子娃娃”。
鄭明鳳把阿克蘇當成了自己的家,把群眾當作了自己的親人,也得到了當地群眾的接納與贊許。
當地有一位63歲的大娘阿依先·莫明膝下無兒無女,鄭明鳳就把她認作了媽媽。
結親的那一刻,他說:“阿依先媽媽,以后我就是您的孩子!”
阿依先大娘把鄭明鳳攬在懷里,激動的淚珠滴落在鄭明鳳的額頭。
這一刻,所有關于民族、血緣、地域、語言的隔閡都已經全然消失,時間定格,留下的只有血濃于水的親情。
“邊疆很遠,但讀懂祖國之后人生會更精彩”

鐘梓歐
鐘梓歐,重慶酉陽人,出生于1989年,2014年7月參加工作,研究生學歷,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外政治制度專業(yè)畢業(yè),現任職于新疆克州阿克陶縣皮拉勒鄉(xiāng)。
碩士畢業(yè)后,放棄內地優(yōu)越的工作生活條件,積極申請到南疆鄉(xiāng)鎮(zhèn)工作。
五年來,先后在阿圖什市阿扎克鄉(xiāng)、阿圖什市團委和平均海拔3500米、邊境線長100多公里的西陲第一鄉(xiāng)——吉根鄉(xiāng)工 作。
鐘梓歐比他們來得更早。
2013年秋季,當時還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外政治制度專業(yè)碩士生的鐘梓歐,正面臨著畢業(yè)找工作的人生抉擇。
政治類學科背景出身,讓他對從事行政類工作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但長期泡在理論學習的“蜜罐子”里,又讓他感覺自己少碰了那么一點實踐的“苦頭”。
機緣巧合之下,鐘梓歐了解到新疆正在招錄選調生,鐘梓歐心動了,對于他來說,山遙路遠的邊疆地區(qū),正是幫助他歷練自我、實現個人快速成長的最佳選擇。
除此之外,邊疆選調在鐘梓歐看來,還是一次“追尋答案”的好機會,回顧校園生活,家國社會總是“活在課本上”,而邊疆選調無疑“能夠更加全面、深刻地認識當下的中國社會,以及面臨的困難和挑戰(zhàn)”。
“(我)想要來尋找問題的答案。”鐘梓歐說。

當地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鐘梓歐始終沒有忘記“到基層去”的初衷,在他看來,“最能展現一個社會全貌的地方就在基層”。但基層工作在最開始也曾讓他感受到想象與現實的落差,實際基層工作中常常出現的各種狀況,也讓他“哭笑不得”。過春節(jié)的時候,鄉(xiāng)里組織每家每戶貼對聯(lián),鐘梓歐給村里的同志交代下去,然而到村里串門的時候,他卻發(fā)現大家把對聯(lián)貼得“千奇百怪”,“想都想象不到”。
類似事件給鐘梓歐帶來了思考,任何基層工作中,干部都要盡可能親力親為,盯著抓落實,因為在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的過程中,一旦中間環(huán)節(jié)出了紕漏,最后的工作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光發(fā)號施令不行,因為基層的情況確實太復雜了,可能到那種情況我再發(fā)號施令,過去的就只有我一個人,或者說寥寥無幾,到最后回過頭,哎,怎么你們還在原地不動呢。”
體會到想象與現實差距的鐘梓歐想到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提到過的“堅持釘釘子精神抓落實”,便把“抓落實”作為自己的首要工作方法,并告誡自己,千萬不能在基層“想當然”。

北大畢業(yè)時的鐘梓歐與在南疆工作后的鐘梓歐
相較于基層工作帶來的“苦”,鐘梓歐認為幸福感是更重要的,而這種幸福感,就來源于與群眾的面對面接觸。
2018年,在北大本科生畢業(yè)典禮上,鐘梓歐作為校友代表被邀請上臺發(fā)言,在演講中,他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基層很苦,但腳底踩泥之后心里會更踏實”,“邊疆很遠,但讀懂祖國之后人生會更精彩”。精彩的演講引起了現場畢業(yè)生同學們的熱烈回應。
對鐘梓歐來說,他希望更多的北大學子到脫貧一線、基層一線、邊疆一線,不僅因為實踐出真知,也因為邊疆基層確實還處在資源貧乏的困境中,需要有更多的人前來貢獻才智。
展望未來,他所希望的并非個人的發(fā)展,而是“新疆形勢會越來越好,而且在2020年的時候能夠跟全國一道完成脫貧攻堅的任務”。
從文凈書生到“毛驢縣長”,從無辣不歡到愛上羊肉,從祖國首都到扎根基層,南疆土地見證著北大人的情懷與擔當,見證著青年人的轉變與奉獻。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一切遠大的理想與抱負,到最后實際上仍然是縮小到自我的完善和對社會的貢獻。
當回首往事時,他們可以堅定地說出:“去南疆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一個決定。”